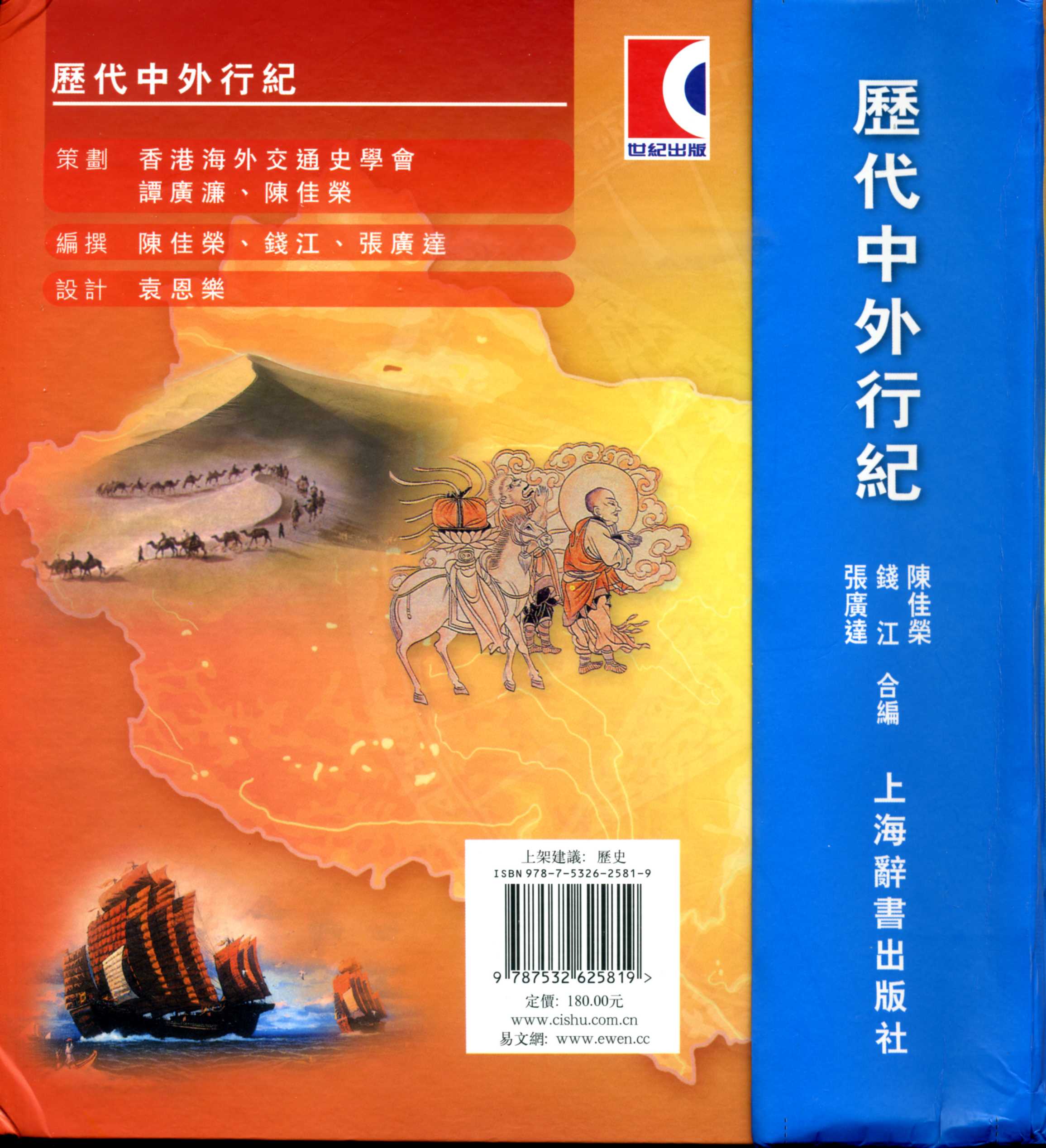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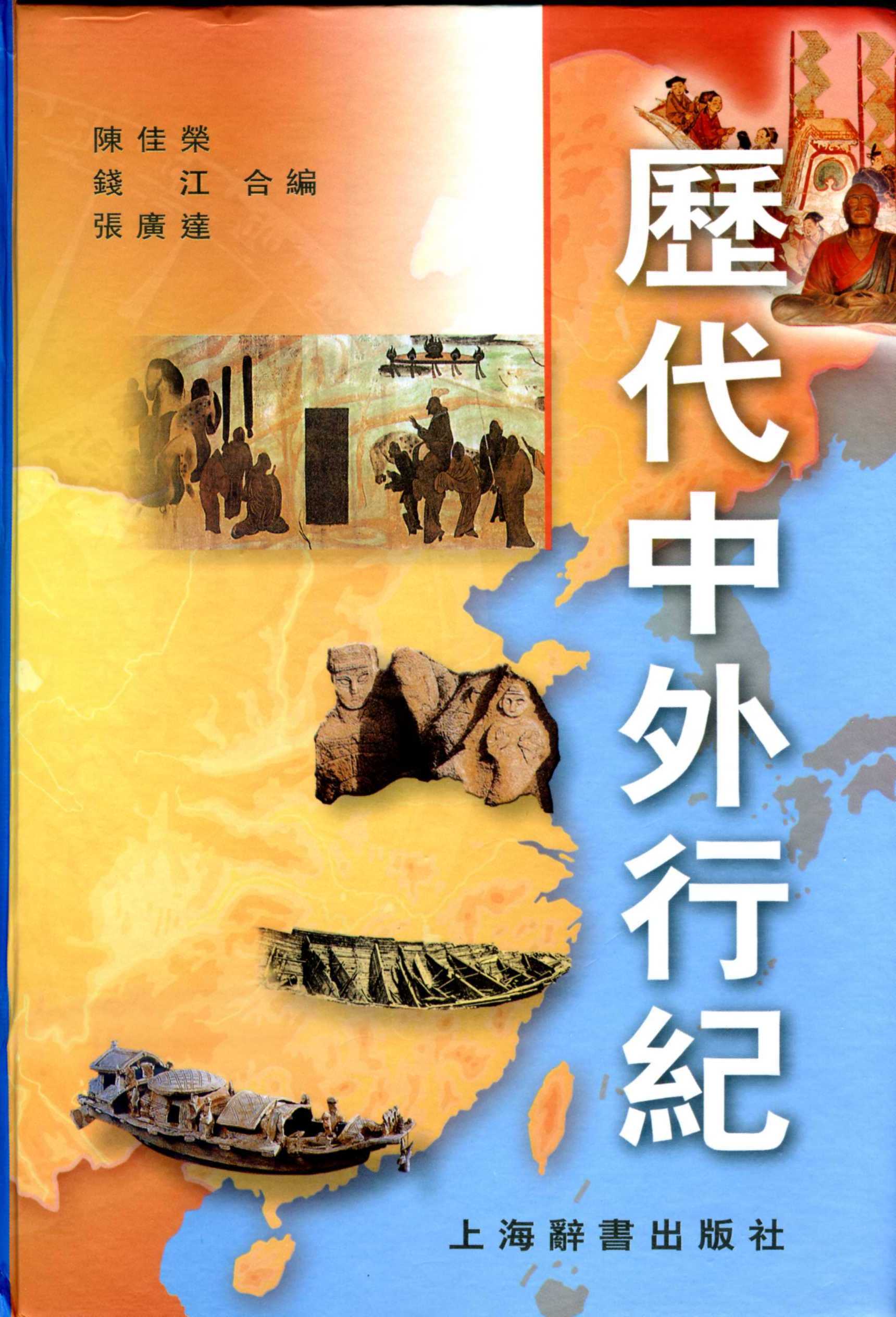

陳佳榮﹑錢江﹑張廣達合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留影﹕中圖-陳佳榮﹔右圖-張廣達﹑錢江2009年6月17日合影
《歷代中外行紀》獲2009年度全國古籍整理優秀圖書一等獎
(後附:評論文章:潘茹红〈重现海洋文献视野下的海洋历史记忆 ——
以《历代中外行纪》为例〉)[2016]
“中國海外交通史籍系列”出版緣起
《歷代中外行紀》出版緣起
《歷代中外行紀》編輯前言
目 錄
*先秦至陳朝
南撫交阯與越裳貢獻
《穆天子傳》等記西征行程
《山海經》中的海內外諸國
徐福揚帆東渡
秦漢經略越地
張騫出關鑿空
西漢遠航印度
印度佛僧入華傳教
兩漢交通海南諸國
漢魏交通朝﹑韓
倭奴通漢及南下裸國﹑黑齒
班超﹑甘英通西域
東漢﹑大秦通交
吳康泰﹑朱應出使扶南
《外國傳》﹑《南州異物志》所記漲海
魏晉南北朝增闢西域通道
法顯西遊天竺及東航歸國
釋智猛之入竺求法
宋雲﹑惠生﹑道榮天竺行紀
高僧東來播教與西行求經
祆教傳入中國
《太清金液神丹經》記眾香國
《職貢圖》記來貢諸國
扶桑僧人慧深來華
南北朝史料中的南海交通
*隋唐及五代
隋征高麗及通百濟﹑新羅
倭國與隋互派使節
劉方南略林邑
韋節﹑杜行滿等出使西域
裴矩圖記西域三道
朱寬﹑陳稜入海探流求
常駿﹑王君政出使赤土
玄奘西遊取經
自張騫至玄奘行紀綜述
《釋迦方志》記通西域諸道
王玄策中天竺行紀
義淨泛舶西航
高僧東來翻經與西國求法
慧超往五天竺
悟空入竺記
唐代與高麗﹑新羅等之關係
日本的遣唐使﹑留學生及學問僧
鑒真東渡日本播教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
怛邏斯一役及杜環的《經行記》
達奚弘通記海南諸蕃及唐籍所載西亞﹑非洲
廣州首設市舶使及海船雲集
蕃教東傳及蕃商入華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
《蠻書》及新舊《唐書》所記中南半島國家
唐代史料中的舍利毗逝及南海諸國
賈耽的邊州入四夷道里記
唐代及其前載籍中的“崑崙”
後晉高居誨之于闐紀行
五代使者所記的契丹 ─ 胡嶠《陷虜記》
*宋遼夏金元
宋代市舶司廣建及絲瓷之路發展
繼業三藏赴天竺記(附《西天路竟》
王延德出使高昌
北印度施護來華
日僧奝 然西渡抵華
北宋征安南與宋鎬出使
注輦娑里三文東來
徐兢等奉使高麗
羅盤始用於航海
海神媽祖崇尚及航海之發展
猶太人大量入居中國
《華夷圖》﹑《歷代地理指掌圖》所載海外諸國
《武經總要》所記赴交趾途程
《文昌雜錄》所記海外各國
《雲麓漫鈔》記諸國舶駛福建
《嶺外代答》所記航海外夷
《諸蕃志》所記海外諸蕃國
《夢粱錄》等筆下的泉州對外交通
《宋史》中的東﹑南﹑西海部分國家
宋﹑遼﹑金時的北部邊疆行記
耶律楚材的《西遊錄》
長春真人西遊
吾古孫仲端北使
宋朝使者眼裡的蒙古
《聖武親征錄》等反映的蒙古西征歷程
常德及《西使記》
元人的北部行記
元軍征伐高麗﹑日本
元軍征緬及與老告﹑暹等關係
元軍三征安南及占城之役
張立道安南錄及徐明善天南行紀
元征爪哇之役
亦黑迷失﹑楊庭璧﹑楊樞出使海外
周達觀出使真臘
《(大德)南海志》中的諸番國
黎崱撰《安南志略》
汪大淵的《島夷誌略》
周致中撰《異域志》
元代陸海對外交通之發達
也里可溫﹑木速蠻及蕃客大量住華
《元經世大典地里圖》及《元史‧西北地附錄》
*明代至清初
《大明混一圖》已載非洲南端
鄭和艦隊七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行程
《鄭和航海圖》等的海外地名
明初經略安南及入交路程
黃福的《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李思聰﹑錢古訓及張洪使緬甸
陳誠﹑李暹等出使西域
吳惠等出使占城航程
崔溥的《漂海錄》(附權近《奉使錄》)
巴喇西國使沙地白入貢
《西洋朝貢典錄》﹑《渡海方程》的針路
《南詔野史》﹑《四夷館考》記通緬﹑泰道
羅洪先增纂《廣輿圖》
明使出訪琉球與釣魚列島歸屬
抗禦倭寇及鄭若曾《籌海圖編》
中﹑日的朝鮮之役
《日本一鑑》所記明中葉海外走私貿易與早期寓日華僑
李言恭﹑郝傑的《日本考》
歐西東漸及傳教士來華
《東西洋考》之海道
《閩書》中的島夷名
諸種海道針經之針路
附﹕(明)慎懋賞《四夷廣記》諸地及針路目錄
顧炎武﹑顧祖禹記海道及諸夷
康﹑雍﹑乾之四方經略
大汕厂翁之《海外紀事》
《安南紀遊》中的入交路程
最早的歐美記遊―樊守義《身見錄》
圖理琛奉使異域
《海國聞見錄》中的東洋﹑南洋及西洋
黎貴惇《撫邊雜錄》所載中越海上貿易
鄭懷德《嘉定通志》所記越南南圻華僑史跡
程遜我﹑陳洪照﹑王大海筆下的吧地
《開吧歷代史記》所載巴達維亞華僑
《海錄》中的海外地名
魏源《海國圖志》(百卷本)目錄(附﹕林則徐等《四洲志》﹑徐繼畬《瀛寰志略》目錄)
清代後期海外紀述名目
附﹕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譯叢目錄
*附錄﹕參考資料
(一) 引書版本
(二) 參考書目﹕中﹑日文﹔西文a-g﹔西文h-p﹔西文q-z﹔俄文
(三) 大事年表
附:評論文章:
潘茹红〈重现海洋文献视野下的海洋历史记忆 ——
以《历代中外行纪》为例〉)[閩南師範大學 2016]
重现海洋文献视野下的海洋历史记忆———以《历代中外行纪》为例
潘茹红
(闽南师范大学,福建漳州363000)
摘要:海洋———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历史进程中有其独特的地位。传统观点一直认为 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其实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文明体,海洋文明是其中的一元,中国 史籍中的海洋图书便是其缩影。《历代中外行纪》一书作为中国海外交通史籍系列之一,大量 收录了相关的海洋图书资料,包含了丰富的海洋历史记忆,如历史上海、洋区域划分的演变, 展现了古人海洋认识的演变;海上贸易管理机构的变迁,体现了政府相关职能的适应能力;指南针及相关针路的出现,是民间海洋力量重整的重要特性。该书所辑录的海洋文献是挖掘海洋图书、认识中华海洋文明辉煌一页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历代中外行纪》;海洋文献;海洋历史记忆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68(2016)02-0084-06
2016年第18卷第2期《巢湖学院学报》No.2.,Vol.18.2016 (总第137期)
Journal of Chaohu College General Serial No.137
引言
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 以来,否认中国有海洋文明的观念支配了史学界的主流意识,海洋意识薄弱,使得海洋文献处于 曲解、贬低乃至失传的境地。其实历代都有与海 洋有关的文献书写,民间航海活动者也有记录。 如何更好地保护海洋文献,重现中华海洋文明的辉煌,亟需整理和运用历史遗留下来的海洋文献资料。
200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陈佳荣、钱 江、张广达合编的《历代中外行纪》,该书收录了 从上古至清初的诸多海洋文献,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历程,虽然编者本身并不是主观意识上的海洋文献整理,也主要是按传统朝代顺序摘录海洋文献,但这些文献包含了古人 对海的认识过程、统治政权在面对海洋时采取的 政策以及民间海洋力量突破封锁的努力等,可以说这本书带有浓厚的海洋气息,为学界整理历史 上的海洋文献提供了参考依据。
——————————————————————————
收稿日期:2016-02-15
作者简介:潘茹红(1980- ),女,福建泉州人。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海洋史学。
1 “海”、“洋”区域划分的演变
海洋是海外交通的载体。《辞海》(1979年版)解释:“通常所称海洋,仅指作为海洋水体的广大 连续水体,一般海洋中心部分叫‘洋’,边缘部分叫‘海’。”[1]这一含义在古代中国有其演变过程,《史记》载“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 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 海求仙人。”[2]这里的“海”应指一望无际的水域。西汉时,随着远航印度洋航线的开辟,出现了专 有名词,如“南海”,在先秦载籍中并没有确切含义,但西汉以后开始用来专指中国以南的广大海域,东汉扬雄《交州箴》将当时交、广一带的海域称为“南海”[3],刘熙之《释名》明确指出:“南海在 海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4]《梁书》记:“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5]。又如三国时期吴康泰、朱应的《外国传》和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书中均出现了涨海字眼,《历代中外行纪》引用了《艺文类聚》《初学记》《世说新语》三书中材料对涨海的描述,“扶南 东有涨海。海中有洲,出五色鹦鹉,其白者如母 鸡”[6]、“大秦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7]、“珊瑚 生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8],陈佳荣等先生在编注中认为“涨海”应是泛指辽阔浩瀚的大海,编者的这一看法大体反映了隋唐以前记录者对海的模糊认识。当然,编者也指出学界对“涨海”一词 的含义仍存争议,如《康熙字典》以之当南海别称;冯承均《中国南洋交通史》以之指暹罗湾南海 域;伯希和、费瑯主张“涨海”指南海西部;许云樵认为“涨海”相当“南洋”的海域,并谓系阿拉伯文献中
“Cankhay”一名之对音[3]。冯承均等人的说法也并非缺乏依据,笔者认为,记录者或许没有明 确的方位意识,但作为航海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如船工之类的人,应该有一定的海域认识,由此 可以推测,在早期与海的交往过程中,古人对海 的认识尚处于朴素阶段。
到了宋代,随着宋人对海认识程度的加深,出现了“海”、“洋”并用的说法。《徐兢奉使高丽图 经》卷三四载录“白水洋:二十九日辛巳,……入白水洋,其源出靺鞨,故作白色”、“黄水洋:黄水洋即沙尾也。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来,横于洋中 千余里,即黄河入海之处”、“黑水洋:黑水洋即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渊沦,正黑如墨”[3]等,这是徐兢 根据“舟人”的描述记录下来的。南宋,众多的官 方、私人记述中已逐渐出现以“洋”代替“海”的情况,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载“海南四郡之西 南,其大海曰交阯洋……其一南流,通道于诸蕃 国之海也;其一北流,广东、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东流,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洋海也……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9],这里须注意的是,宋人对“海”、“洋”的认识并不简单只停留在此, 一些著述里出现了“东洋”、“南洋”、“北洋”字眼, 真德秀《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载“永宁寨……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自南洋海道入州界,……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3],这种以 泉州港为本位提出的海域划分,是泉州港海外交通的实践形成的,吴自牧《梦梁录》载“若欲船泛 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 也”[10]。
到元代,“海”、“洋”的认识更加明确,元代典 籍中出现了“西洋”字眼。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中载“嘉兴人【杨】君讳枢……以官本船浮海至西 洋”[11];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中也提到:“其国中虽 自织布,暹罗及占城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 者为上”[12]。“西洋”一词的出现,说明元人对海外地理的认知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此外,陈大震、吕 桂孙所撰的《(大德)南海志》同时提及了“东洋”、“西洋”,如“单马令国管小西洋、三佛齐国管小西 洋、东洋佛坭国管小东洋、单重布啰国管大东洋、阇婆国管大东洋”[13];汪大渊《岛夷志略》也提到了 “东洋”、“小东洋”和“西洋”,如“贸易之货,用西 洋布、青白处州瓷器”;“自有宇宙,兹山盘踞于小 东洋”;“爪哇即古阇婆国……实甲东洋诸蕃”[14]。此时的“东洋”、“西洋”是元人根据航路的先后、远近对东南亚诸国地名的排列。依照《(大德)南海志》和《岛夷志略》两本书的记载,《历代中外行 纪》编者考证后认为:“元代东、西洋的划分应是以广州-加里曼丹岛西岸-巽他海峡为界划分,加里曼丹岛、爪哇岛及其以东地区、水域为‘东洋’, 其中加里曼丹岛北部至菲律宾群岛一带为‘小东洋’,而‘大东洋’的范围则西起巽他海峡,中经爪哇岛,加里曼丹岛南部,苏拉威西岛、帝汶岛,直至马鲁古群岛一带。‘西洋’的范围东自加里曼丹 岛,爪哇岛西岸起,向西直抵印度洋,其中又以马六甲海峡为界而划分大小西洋,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一带为‘小西洋’(约当南海西部),印度洋为‘大西洋’。”[3]笔者认为,《历代中外行纪》编者的这种认识是对在元代海外交通充分发展的 基础上所呈现的各类海洋图书的总结,明初郑和下西洋就是以这种海域认识为指导的大航海。晚明张燮《东西洋考》一书提及“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15]①(即隆庆开海后月港官方对东西洋范围的认识大体遵循元时的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关于东西洋界限的划分,学界仍有争议,前述陈佳荣先生在其《帆船时代南海区划东西洋之另一讲究》一文有所扩充
当然,明代航海所至的东洋范围还包括官方严禁的日本、从福州朝贡的琉球国,因非官方指定为 月港出海目的地,未被张燮记录。又胡宗宪主编、 郑若曾撰《筹海图编》载“太仓生员毛希秉云…… 然闻南洋通番海舶……他如南洋、西洋诸国,其 隔闽、广也,近则数千里,远则数万里……非若南 洋、西洋一望无际,舟行而再不可止也”[16],这则材 料中的“南洋”已不是宋时以泉州为本位的认识, 其含义更贴近近代的含义。
清初,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提及的东洋、 南洋及西洋,可以说是宋元出现东、西、南、北诸 洋名来,最为系统的关于各大洋的著作,该书详 细介绍了东洋、东南洋、南洋、小西洋、大西洋诸 国内容,分别见于《海国闻见录‧东洋记》《海国闻 见录‧东南洋记》《海国闻见录‧南洋记》《海国闻见录‧小西洋记》《海国闻见录‧大西洋记》等条目中[17]。陈佳荣先生等人认为《海国闻见录》这本书 是明末清初地理新知识的总结代表,其记述遍及 今欧、非各国,它与稍后的《海录》,是宋元以来记 述海外交通最重要的著作,大致反映了清时国人 的地理认识水平。
可见,从先秦到清初,《历代中外行纪》一书 所辑录的众多海洋图书中的文献资料集中反映 了古代国人对海洋认识的逐步明确:隋唐前对大 海的懵懂认知、宋元时海的范围的明确、明清时 期方位概念的准确运用。
2 海上贸易管理机构的变迁
秦汉至唐初,朝廷并没有明确的海洋意识,航海贸易只是经济形式的补充,朝廷并不设置专 门机构负责海上贸易,对外贸易由少府兼职负 责,“南中有诸国舶……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 值,市了,任百姓贸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 进内”[18]。唐中叶,随着海路交通与海外贸易的发展,专管海上对外贸易的官职———市舶使,应运而生,《旧唐书》记载“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 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19]①;(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也提及:“【广 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 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 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 多”[20]。上述两节材料反映了市舶使的设置与当时 广州海外贸易繁荣的关系。作为专管官职,如何管理在史籍上也有记录,(唐)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則本道奏 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 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21],这一记录规定了市舶使的职责是“纳舶脚”、“禁 珍异”。市舶使的设置及其职责的规定,反映了唐代海上交通的发达,当然,此时的海上交通多以 阿拉伯势力主导为主,市舶使的设置是适应当时 环境的产物,唐政府还没有充分的主动意识发展 海洋经济,这一意识直到五代才开始出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安南市舶使之安南,据陈佳荣先生等人考证,应为岭(广)南,见《历代中外行纪》:329
宋代,随着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市舶司”这一专门机构并规定了它的职责,《宋 史》记载:“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 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元祐初,诏福建路于泉 州置司”[22]。相比较于唐代,市舶司这一专职机构 的出现,反映了宋朝政府发展海外贸易的决心。为了更多的获取贸易利润,政府设置市舶司的地 方不断增加并制定了相关的管理规定,“【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 交趾、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市舶 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淳化二年,诏广 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元祐三年……置密州板桥 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崇 宁元年,复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旧额。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勿杂禁物、奸人……凡海舶欲至福建、两浙贩易者,广南舶司给 防船兵仗,如诣诸国法。广南舶司鬻所市物货,取息毋过二分”[23],这段记载反映了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繁荣,沿海各个港口逐步开放以及宋朝不断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和掌控,这种强化管理折 射出宋一代以国家为主导的海_洋政策的强力推行,此时也是中华海洋文明繁荣的重要时期。
到元代,元政府除设置市舶机构外,还制定了许多措施鼓励对外贸易,《元史》记载:“元自世 祖定江南,凡临海诸郡与蕃国往返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于是至元三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 ……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 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杂禁,凡二十二条 ……独泉州于抽分之外,又取三十分之一以为 税。自今诸处,悉依泉州例取之”[24]。此外,在元代市舶条例22条中还规定:“舶商、稍水等,皆是趁 办课程之人,落后家小,合示优恤,所在州县并与 除免杂役”[3],元政府的这条规定突破了一直以来 传统社会对渔民、船工一类人群的蔑视,对于长 期游离于主流社会的渔民来说,这种身份认同是一鼓励。由此可见,市舶司制度从初创到逐渐完 善,并形成一种专门机构的发展过程及政策取向, 实际反映了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控制由松而紧, 并日益倚重的演进历程[25]。宋元时期海洋经济的 活跃程度,决定了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而这些政 策的制定,又刺激了宋元海洋经济的深入发展。
明朝初建时,因政权需要,曾一度实施海禁 政策。永乐年间,随着朝贡体系的陆续恢复,政府 恢复和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永乐元年八月,令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 举司。永乐三年九月,以海外诸蕃朝贡之使益多, 乃命福建、浙江、广东市舶提举司各设驿以馆之, 福建曰来远驿,浙江曰安远驿,广东曰怀远驿,各 置驿丞一员”[3]。
至此,《历代中外行纪》所纳文献综合记载了秦汉至明初古代中国在发展海外贸易方面所做 的努力,市舶司这一管理机构的建立、发展、变革 是官方主导海洋政策不断变更的体现。
3 指南针与航海针路的应用
宋以前,海外贸易在中国并不占据重要地 位,其很大因素取决于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水 平。在早期的航海活动中,由于技术的限制,更多 的是依靠大自然判断方向,《法显传》载“大海弥 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26],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 法显的远航风险是不可控的,也正因为风险的未 知性,通过海道进行交往的活动在当时被视为畏途。到宋代,航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曾 公亮、丁度《武经总要》中记载“若遇天景噎霾 ……或出指南车及指南鱼,以辨所向……用时 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 向午也”[27],沈括《梦溪笔谈》提到:“方家以磁石 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不若缕悬为最善……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28],朱彧《萍洲可谈》进一步提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29]。 三则材料指明,在宋代,我国已出现了指南针,指南针本身的运用、完善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当然, 指南针真正运用于航海活动的明确记载是徐兢 《奉使高丽图经》,书中记載到“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①对于指南针运用于海上的记录,南宋著述 频繁出现,赵汝适《诸蕃志》提到:“舟舶往来,惟 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30],吴自牧《梦梁录》“风雨晦暝时,惟凭针盘 而行……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31]。为 此,《历代中外行纪》编者提出:“通观宋一代诸书,徐兢《奉使高丽图经》是最早明确记载中国海 船如何使用指南针导航并行走于专门航海上的书籍。”[3]
————————————————————————————
① 据陈佳荣先生考证,句中断句应为“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此说法更为确切 。
指南针的运用,促进了宋以后海外交通的繁荣,为后来的针路记录提供了条件,而针路记录 的出现,又促进了航海活动的开展。明代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中提到:“惟观日月升坠,以辨西 东,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刻木为盘,书刻干支 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要在更数起止,计 算无差,必达其所”[32]。《西洋番国志》是郑和下西 洋随行人员巩珍的著述,书中提到的针经图,是 考察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资料,反映了明初指南针已普遍运用于航海活动中。黄省曾《西洋朝贡典 录》里也有相关的针路记载,如爪哇国第三中提到:“自泉南登州,行者先至占城,后至其国,针位 ……五十更曰蜈蜞之屿……又五更取竹屿”[33],此 外,茅元仪《武备志》详细记录了郑和下西洋往返路程的针路及过洋牵星图[34]。当然,关于明代的针路记载,还可以参考张燮《东西洋考》一书,书中 卷九舟师考中记录了“西洋针路”、“东洋针路”, 如“西洋针路”南澳坪山条中提到:“用坤申,十五 更,取大星尖”[15],又如“东洋针路”太武山条记录: “用辰巽针,七更,取彭湖屿”[15]。这里须明确的是因张燮本人并未涉足海外,书中对针路的介绍, 应该是明初以来漳州一带有关航海针经记录的 引用。张燮,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人,著名的民间贸 易港口月港位于此地,《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提 到:“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35],嘉靖时,月港地方已达到“方珍之物,家贮户藏,而东连日 本、西接琉球、南通佛朗、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 绣蹑球”[36]的地步。正因为月港民间海外贸易的繁 荣,船家留下许多关于航路的记录,也就为张燮 撰写《东西洋考》提供了便利。此外,漳州船家使 用的《顺风相送》[37]等的针路记载,也是了解明代 航海图经的途径。
通观明一代,开国时的海禁、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表面繁荣、郑和下西洋后的全面收缩,明朝 政府在航海活动中扮演了消极的角色,限制了官方主导的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但这一情况并没 有影响民间航海活动的深入开展,明中叶后以针 经路簿为典型的海洋文献是这一海洋发展局面 的最好见证。
结语
海洋是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质疑中华海洋文明的存在。其实,纵观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华民族在认识海洋、开拓海洋的过程中创造出了辉煌的中华海洋文明。在这一 历史链条里,出现了大量的海洋文献,但因缺乏对海洋文明和海洋意识的足够认识,很多海洋书 籍湮没于历史长河中,以至于缺乏对它们的基本 了解和掌握,《历代中外行纪》一书的编者从海外 交通史的角度辑录了大量的海洋文献资料,为整理历史上的海洋文献提供了线索。
綜观《历代中外行纪》一书,其所引用的海路资 料,以不同类型海洋活动参与者为别,涉及了不同类型的海洋文献,如第一类,海洋活动直接参与群体或称为“海洋生存倚靠者”所撰写的文献 图书。这类书籍包括了如船工、渔民使用的针路、 海商的记录,这一类是最主要的,也可以说是最 真实的海洋文献;第二类,坐船者所撰写的海洋 书籍。这涵盖了商人、游历者、宗教人士、使节等人所写的著作,他们算是比较直接的海洋活动参 与者;第三类,陆地文人关于海洋事项的介绍、研究。这类书籍包括调查海洋的记录、陆地思维写 的海洋图书、沿海知识分子写的海防书籍等,在这书籍中,隐含着作者对海洋的认识与态 度,这些海洋文献撰写者的立场以及书中的内 容,是分析海洋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一部分的重要 媒介。当然,历史上的海洋文献远不止这些,不同 类型的海洋文献,包含了中华海洋文明发展过程 中的诸多内容,有待学者们继续挖掘,得到更多 的海洋信息,从而证明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特征 以及海洋文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
参考文献:
[1]辞海:中[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2157-2158.
[2](汉)司马迁.史记:卷6[Z].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特精装本:247.
[3]陈佳荣,钱江,张广达,合编.历代中外行纪[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28、62、432-433、440、490、639、675、711.
[4]任继昉,纂.释名汇校[M].济南:齐鲁书社,2006:87.
[5](唐)姚思廉,撰.梁书:54[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特精装本:783.
[6](唐)欧阳询,著.汪紹楹,校.艺文类聚: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575.
[7](唐)徐坚,等,著.初学记:上:卷6[M].北京:中华书局,2004:115.
[8](南朝宋)刘义庆.(梁)刘孝标,注.杨勇,校签.世说新语校签:修订本: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6:791.
[9](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9:36.
[10](南宋)吴自牧,著.傅林祥,注.梦梁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170、171.
[11]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5: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 1313: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53.
[12]陆峻岭,周绍泉,编注.中国古籍中有关柬埔寨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
[13](元)陈大震,纂修.李勇先,校点.大德南海志[M]∥王晓波,等,点校.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8.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社,2007:58-60.
[14](元)汪大渊,著.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1:38、135、139.
[15](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2.
[16](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171、182、458-460.
[17](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35-69.
[1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364:政书类:第606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52.
[1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8[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特精装本:174.
[20](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74.
[2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341:小说家类:第1035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49.
[22](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67[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特精装本:3971.
[2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86[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特精装本:4558-4561.
[24](明)宋濂,等,撰.元史:卷94[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特精装本:2401-2402.
[25]黎虎.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J].历史研究,1998,(3):29.
[26](东晋)法显,著.章巽,校注.法显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67.
[2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32:兵家类:第726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68.
[28](北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68.
[29](宋)朱彧,撰.萍洲可谈:丛书集成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
[30](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216.
[31](宋)吴自牧,着.梦粱录,校点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32](明)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3](明)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0:18.
[34](明)茅元仪,辑.武备志:卷240: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M].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10177- 10223.
[3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7:大陆版[M].济南:齐鲁书社,1997:57.
[36]陈自强.论明代漳州月港[C]∥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月港研究论文集.厦门: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1983:1.
[37]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0.
REEMERGENCE OF OCEAN HISTORICAL MEMORY IN MARINE LITERATURE
-BASED ON HISTORICAL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ISSION
PAN Ru-hong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venue for human activities,ocean has a unique position in history. Traditional view claims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ctually ocean civilization plays a major rol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could be proven in ocean books. The book-Historical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ission,records lots of ocean books,including plentiful ocean messages,such as the reorganization of sea,the vicissitude of trading mechanism on the sea, the appearance of compass and the needle passage and so on. Therefore the progress of China ocean civilization can be reflected from the ocean books.
Key words:
Historical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ission;marine literature;ocean historical memory
责任编辑:李晓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

